日本人不愿承认是亚洲人
by Yan
看到以下这篇文章,留作参考。
------
大陆观念淡漠 强调大国身份
日本人不愿承认是亚洲人
[日]拉梅什·塔库尔 井口高志 蔡
日本经济比亚洲邻国强大很多
欧洲大陆位于英国的南方和东方,亚洲大陆则在日本的北方和西方。英国有家报纸曾经用这么一个很有名的大字标题抒怀道:“迷雾弥漫在英吉利海峡的上方,大陆被我们排斥在外面了。”日本人也许不像英国人那样极度地自以为是,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它的文化和民族远比英国(尤其是现代英国)更为单一,也更为封闭。
日本在地理位置上离亚洲大陆更为遥远,但是从某种角度说,比起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距离,日本与亚洲大陆的距离要近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失去了帝国地位,但是赢得了在国际上的角色。太阳永不落的大英帝国成了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仅是欧洲的一个成员。而在这场战争之前,日本赢得了帝国的身份,但是它因为在二战中痛苦的、彻头彻尾的失败而失去了自己在国际上的角色。日本,这个实际上太阳很快就落下的帝国,它依然只局限在亚洲的范围内。
英国人对待欧洲大陆所有事务的优越态度就是建立在”我是世界一员”的基础上,而日本与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双边关系,目前依然笼罩在日本的殖民主义历史、以及当年它对这些国家残酷政策的重重阴影下。
亚洲现在开始谋求更为庞大的地区经济一体化,那么日本会在其中发挥作用吗?日本与亚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存在差异,这使得日本与这些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双边协议时非常棘手。这种双边协议对于提高签约国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双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通过相辅相成的经济原则而实现。日本知道自己的经济比亚洲邻国强大很多,日本官员对这种经济差别心里很清楚,因此才有了今天这种对待亚洲伙伴的态度,即从内心不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员。
只有26%被调查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亚洲人
身份认同这一心态是复杂而多变的,正如最近10年里我们在巴尔干半岛和东帝汶看到的变迁那样。现代日本有很多东西都是长期以来从亚洲借鉴发展而来的,对中国的借鉴最为明显,但并不仅限于中国,也有从印度吸收的东西,如佛教的影响。尽管日本现在远远把自己的亚洲大陆身份抛在脑后,把自己当成了西方工业国家的一部分,而不承认是工业化尚未完成的亚洲大家庭的一员,但是,由于日本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军非常成功,人们可能也就原谅了日本的这一想法。
所谓身份的认同,是指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情感获得安宁、也准备为这种认同做出很大牺牲的东西。一个国家在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时,身份认同这一心态往往会从中起作用。
2000年,笔者(井口高志)对18个国家(包括9个亚洲国家和9个欧洲国家)进行了一项国际调查。结果发现,有2/3的日本被访者认同自己是日本人,有88%的韩国人认为自己是韩国人,但是只有26%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亚洲人,而有高达80%的韩国人认同自己的亚洲身份。
原因很简单,传统上日本人对自己亚洲身份的认同一直就很淡漠。日本人对待大陆的态度,与英国人很相像。“不要同大陆亲近!”这是描述它们同大陆关系特征的最好的习惯用语。对日本和英国而言,各自的大陆就是一个潜在的出麻烦的地方。他们认为:只是出于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方面的因素,才需要与大陆打交道。
在日本这个民族文化单一、且具有强烈排外情绪的社会,萨缪尔·享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在读到享廷顿把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区分开来的章节时,许多日本人感到很受用,很舒服。
但是归根结底,英国人和日本人还是大陆人。与他们对自己大陆身份的否认形成巧妙对照的是,英国人和日本人均是从事海运贸易和全球贸易的民族,都是彻底的自由贸易商人,都是与大陆密不可分的。
通过与美国结盟取得身份认同
英国和日本政府都不赞同各自国家中压倒多数的反战情绪,它们坚定地支持美国推翻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政权的政策,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框架外对伊拉克发动的这场战争。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有两个盟国出兵与美国人并肩战斗,一个是澳大利亚,另一个就是英国。日本尽管在伊战期间没有出兵,但是目前日本政府已通过了适当的立法,为派遣自卫队到伊拉克维护战后稳定铺平了道路。从这个例子来看,英国和日本都相当重视从战略高度上与美国建立双边联盟,尽管它们支持美国的背后也有“必须推翻萨达姆、解放伊拉克人民”这一信念的支撑。此外,这两个国家还考虑到,从内部影响美国的决策更为实用,而不是从外部进行无效的批评。换句话说,日本和英国都通过与美国结成强有力的联盟,而不是与他们各自大陆的邻国结盟,来认同自己的身份。
但是,跟英国受到欧洲大陆局势影响一样,日本也势必受到亚洲大陆局势的影响。伦敦和东京各自都与华盛顿建立起了亲密和重要的安全联盟,但是在大陆各种政治潮流的冲击下,它们不能只关注与华盛顿的关系,也试图平衡这个联盟,因此,伦敦—华盛顿的“英勇轴心”就在“伦敦—巴黎—柏林三角”这种范围更大的国家间关系中获得具体的体现;东京—华盛顿轴心也发展成了东京—汉城—北京框架,并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发挥和演绎。▲(摘自11月9日《日本时报》)(拉梅什·塔库尔:东京联合国大学前副校长,井口高志: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环球时报》 (2003年11月24日 第十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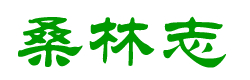

“有2/3的日本被访者认同自己是日本人”
那另外三分之一是哪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