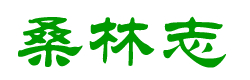小狗
by Yan
小狗
一
我希望这个故事能完成。
我要讲的故事大约是高中时的事情,从一条小狗开始。这条小狗昨天进入我的回忆,又勾起很多往事。我想从它开始讲,也许可以说出许多美好的事。其实,事情美好不美好并不重要,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都会在我心里滋长甜蜜。我现在25岁,所以写高中时的事情正好合适。我现在经历的事情应该由我中年时候来写。就是这样,材料需要经过搅拌,然后发酵,再象抽丝一样慢慢地把它们取出来。
今天是五月四日,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外面该有许多活动吧,我不知道。我准备呆这间屋里,写不知道怎么发展的文字。窗外正在修路,搅拌机发出不间断的声音,听多了会让人恶心。所以我戴上耳机,听听磁带。我听的是“Bear’s Choice: History of The Grateful Dead ( Vol.1)”。外面阳光很好,春天天气。窗台上三盆花沐浴在阳光里,两盆虞美人,一盆刚插的彩叶草(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叫,因为那位老太太也不确定,我向她要的)。电话就在边上,随时会响,因为我刚跟一个人说,今早我不出去,而他上班很轻松,打电话很方便,跟我关系又象是小玩伴。
那条小狗进入我的生活是高一时的事情,严格说来,它进入的是我们班的生活,高一(四)班。它那天在学校东南角一个小木门那儿惨惨地叫。我们班就在边上,一个三层楼的一层。在我们班上面是一个医护班,有许多漂亮的女同学(不称“女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比我们大。如果以现在的德性,会毫不犹豫地叫她们姐姐。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想下面抽空再讲。
那条小狗在门后面叫,应该用“吠”字,这才充分利用了汉字的形象性。它用两只手扒拉着木门,好象是刚被主人扔进来的样子。我注意到它了。我当时在干什么呢?我真是想不起来了。但我有印象,当时空气里有一股清香,槐花的香味。这样说来,该与现在的季节差不了多少。一串串的槐花又香又好看。我们攀枝条采。这大约又是高二时的事情了,因为高二的教室在二楼。槐树种在楼前,树冠伸展开来,有些枝条我们在走廊上伸手就能抓到。采到花,我凑到鼻子边上闻闻,应该马上送给心仪的女同学,但当时我是不敢的。
整个校园浸在槐花的清香里,早晨的太阳透过绿色的树冠闪烁着光芒,空气清新而湿润。我对槐花的香味之所以这么印象深刻,是因为我现在所在的校园里也有槐树。花开的时候,白天也许闻不到,但夜晚,当我从实验室出来,骑车穿过校园,那香味浓极了,象是静止的,化不开的。
我的眼睛当时还很明亮,跟天空一样清澈。我跑过去摸了摸它的脑袋。我不会和它说话的,我不爱说话。它的身体柔软极了,我一手撑在它一边的腋下,把它抱到了教室里。
同学们这时应该都围上来了吧。我能记得的是,有一个女同学也来招惹它,但又怕狗。结果它朝她凑过去,她吓得跑,它就在后面追。她就在教室里转圈子,嘴里哇哇叫,脸上一副要哭的表情,我们大家都笑。
小狗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但持续不到一个月的样子,这你将会看到。我们把它带回了宿舍。我们宿舍有十二个床位,住了八个人。它来了,就是九个小东西了。它没有占剩下的空床位。它在一个角落里定居。我们给它布置了一个很舒适的窝,包括几块废弃的破棉花毯子和一些硬板纸。它还是很爱干净的,自己的窝里没有留下屎与尿的痕迹,整个屋里也没有。后来我们发觉了它的规律。它拉屎的地方是在宿舍楼前面的花坛里,而撒尿的地方是在隔壁宿舍,就是我们班的另一个宿舍。因为他们常闻到一股骚味,后来发现床底下一滩滩的尿迹。他们很生气的样子,把我们给乐坏了。它真是我们的小宝贝。其实,它也是他们的小宝贝。
我还没有做它的肖像描写呢。它有什么特别么?我感觉不到,就象小时候觉得老外都长一个样一样。想起它来,就能看到它专注的黑眼睛,有时候忧郁,有时候神采飞扬。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它的眼睛象小孩子的一样被食欲催得紧张。黑鼻子湿漉漉的,在宿舍里走来走去,向我们每个人要吃食。我们如果有肉吃,骨头当然是它的,有时候也爱惜地给它肉吃。要是给点米饭,它也吃。其实它不会饿着的,学校食堂附近到处是剩菜剩饭。我们常常见它吃饱了,在花坛的美人蕉下面钻来钻去。
它是一条黄、白两色的花狗,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给它取名字了。它属于我们那儿常见的品种,身材不高不矮,再怎么长也不会特别结实的样子,象羚羊一样轻盈。它那时候还是条小狗,在我们一起生活的期间,长大许多,但到最后也称不上大。
它的性格?我觉得它的性格很好,不懒也不张狂。它象一个早熟的少年的样子,眼里老透着忧郁。也有快乐的时候,就是与我们一起飞奔。和它一起飞奔是我们挣着要做的,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下次序,今天是他,明天是他。与它一起飞奔,下午去上课时,与它一起飞奔着穿过操场。我们和它都会觉得很快乐。
二
现在是下午,刚刚午睡起来。外面阳光很好。工人们在装石子,那些昨天从一辆大卡车上卸下来的。很吵,我又戴上耳机,换了一盘磁带,这次是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再来说,我与小狗一起飞奔着穿过操场,我们都很快乐。这种快乐是基于身体的,也许来源于肌肉的一张一缩,骨节的转动,脚掌与大地的磨擦。象是在草原上飞奔,鸟儿在空气中飞翔。但是,学校的操场没有草。
我们大约就是这样与它玩的。去摸它的背,用手引诱它,它跳跃着,有时只用后腿着地,我们和它眼里都在笑。但最印象深的还是奔跑,奔跑。它还是条小狗,但跑起来真美。
星期六,我们都要回家。小狗只好被关在了宿舍里。现在我会想,它一只狗呆着多可怜,可当时并没有这么想。星期天晚上回来,屋里一塌糊涂。其它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住下铺同学的蚊帐都被撕破了,我住上铺没事。不知道经过这事后,他们对小狗的感情是否就不如以前了?我想不起什么迹象来说明答案是“是”还是“否”。反正我没受影响,我对小狗的感情一如既往。
后来有更大的麻烦了。我们要放好几天的假,好象是农忙假,相当于春假。我们大多是农村来的,得回家帮忙。小狗怎么办?大约我们曾经为此讨论过,后来的办法是由班长领回去养几天。这说明这条小狗已成了我们班级的一员,也处在班长的管辖和爱护之下。我又想起一点来,我们与它一起玩,似乎也有一点在女同学面前表现的意思。表现的什么?我们的同情心?我们与狗一样的野性、活力?我想都有一点。
班长在放假结束后,又把它领回来,它没有变样,不,它大了不少。班长说,他把它养在家里的阳台上。我去过他家,与他在阳台上下过棋。还可以吧!它活的不错,可以整天看着面前一条河上的船只来来往往。下面是条街,我希望它朝路上行人叫,又往下撒尿。小狗的叫声,我一直印象深刻,也许是那时侯得来的。
这样的好事当然不会长久,中学时碰到的所有好事都不会长久。班主任说,宿舍里怎么能养狗?学校里怎么能有狗的存在?你们在某某日之前把它处理掉!
我不说我们如何如何伤心了,都差不多,差不多。不管怎样,我们都得照办的。
第一次,我们把它领过那扇门,然后突然关上。当初就是在那儿,我发现它的。但这次是在门的另一边。他呜呜叫着,和上次一样。只是声音象大狗一点。用手抓着门,我们在教室里上课都听见啦。第二天,我们发觉它还在那儿。
三
现在是5月8日下午了,有几天了吧,把这个故事放在一边。其中的原因离题实在太远,不好在这儿说了,虽然说说也没什么关系。前面提到过搅拌机,现在它还在那儿转呢,能听见石子与水泥、沙子的混合物滚动的声音。路只剩一点点没修完,民工,灯泡,沙堆,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已建立起来。
说小狗的事情。前面这几天,我特别注意了槐树,槐花正开呢!夜晚,路灯下的香气,我骑自行车走过,象是刺破了一块绸。甚至,在大白天,太阳底下,我也闻到了,因为我注意的缘故吧!这种香味帮助我联通记忆里的不同时刻,而这一连串的场景中排在最前面的是与小狗有关的。
这几天,还好,怀旧的情绪始终没有完全撤离。5号那天,我在马路边上看见有人在卖玉兰花。我很惊讶,我应该讲很想买几个挂胸前的,但我没有停下车。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似乎在赶往一个目的地而无暇为吸引我的事物停顿了,而实际上出于一种反应的滞后。玉兰花也与我的中学时代联系在一起,它的简洁的线条,它的清雅的香味,以及它别在胸前纽扣上的形象,一直印在脑海里。
回头再来说我的故事。小狗第二天还在那扇木门的另一边,它再不叫了,没力了吧,它也知道叫是没用的了。它脸朝着门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它在等着门开开,闪出一张小脸来。它在并不发达但足够感受的脑袋里已经反复幻想过这样的场景了,幻影已经定型下来,这时候幻影成了另一种真实。它会为了它一直这么等下去,算是钻进了牛角尖吧。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外力把它从这种状态(一个势井里)击出来,它会饿死在那儿。说起来,这多象一个痴情的恋人。
我们透过木门上的裂缝看到了它的这个样子。我们心里不好受,我们还是小孩子,所以打开了门。它一下子站起来,摇头摆尾的,但还站在原地,眼睛盯着你,表情还是很悲哀的样子。它还在试探吧,或许我们与它之间已有了隔阂,它本能地就明白这个,它不希望这样,但隔阂就是在那儿,它毫无办法。我们蹲下来,用手扰扰它的头,它于是过来,身体紧贴你的腿。这样,它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但我们必须把它打发出去。
上面用“我们”在逻辑上是不对的,这些事情怎么能由复数个人来做呢。但我不想在大伙儿间区分我与他等等了。我强烈地感受到,我在叙述这件事情时,代表的是“我们”。
然后有了第二次把狗“处理掉”的事情。这次我没有参加,我只是通过他们(做这件事情的同学)回来后的零星的话语中知道一点情况。他们把它引到小镇的另一边,东北角?我们的学校在西南角。它很欢快,或者在前面走,或者落在后面,但不会超过一定的距离。从某种意义上说,带一只狗出去散步和带一个调皮的小孩一起去散步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他们在它离他们比较远时就试图甩掉它。他们努力了好几次,才完成了任务。他们跟我们(没出去的人)说,它很傻的,不知道他们在找机会甩了它。
第二天,我们上完课回宿舍时,发现它又在门口了。它欢快地摇着尾巴似乎又有点不好意思。它不知道它是被甩掉的,它以为是它自己走丢了。它再见到我们,它很快乐,又觉得抱歉:让我们担心了。而它竟然能自己找回来,对这件事它一点反应也没有:这又有什么奇怪的?我们抚摸着它,喂它食,与它玩,心里感动着不同的感动。
事情变得难办了,但我们不可能违抗班主任的意思的,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把它“处理掉”。
我们又带着它出门了,这次我似乎也在其内。我们走出校门,经过了哪些地方?菜市场,横街,石板铺的巷子,一座又一座的桥。桥两侧的石头缝里长出许多草与树来,其中有一棵石榴树,有一年还开了花。我们到一个码头上,运粮的码头。对岸,停着一只小木船,两边舷上停着两只墨鸟。不知道谁在这时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不是我吧。把它放船上,这样它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把它放在一条运输船上,很大的。后部是驾驶舱和机动部分,中部和前部是一个大船舱。舱里往往放满了货物,象成包的谷类或水泥等,散装的石子,沙子等。使船吃水很深,好象一个小浪头打过来,就要进水的样子。我们应该是把它放在这样一条船上了,因为我印象里常有一条不大的小狗在这样一条船的船舷上走来走去,常常是被一条绳子拴住的,怕狗掉水里吧。
四
又休息了一会儿,再回过头来写我的故事。外面是民工用铲子铲沙石的声音,我已经听了近一个月了吧,朋友戏谑说:“你都适应了吧!”再往远,操场上在开运动会。老调调,咚咚咚咚一阵阵的擂鼓声,广播里发着这样的噪音:“···参加400米接力的同学马上到检录处检录···”。为了躲避声音的打扰(我已拉上了窗帘挡住了光),我又戴上耳机。听什么呢?这回我选的是罗大佑《恋曲1980-1990》。老带子了,水木清华BBS上火车和小they几天前说起过其中的一首歌《鹿港小镇》。怀旧的调子,旧时的带子,旧时的歌声,很适合我现在边听边写这个故事。其中一首《爱的箴言》让我想起了一个同学,那是大学毕业时候的事了。他老唱这首歌,我还傻乎乎地和他合唱过一次。后来我明白,他当时唱这首歌是带着怎样的感情啊。而我现在回忆起来,会为当时的我感到尴尬。为什么会选择听这盘带子?是不是也受我要把它写进文字里的影响。影响是肯定的,但具体影响到怎样的程度却永远不会知道的,因为我不可能知道如果我不把它写进文字里我会选择听什么磁带。呵呵,说着都饶舌,还是马上回到我的小狗上去吧。
小狗它被我们放到上述这样的一条水泥运输船上。说到这儿,我脑子里浮现的画面是:它蹲坐在靠我们这边的船舷上,眼往着我们。眼神是什么样子的?我思想的目光却怎样也不能集中在它的面部了。同样的,脑海里也只有这一幅安静的图象,怎么可能没有叫声,怎么可能没有叫得撕声裂肺的?但我的脑子却把这一部分给紧闭住,不让我往里偷看一眼。或许根本没有,或许我根本就没去。可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认定自己也去了呢?废话!废话!我要说的是,我受不了它的可怜带给我的刺激,所以这些图象和声音被压进了无意识。然后就能接着推出,我是一个多么有同情心的人啊!我是多好一个人啊!呵呵,我要说的其实就是这个,拐弯抹角的。
我们就这样把它“处理掉”了,它再也没有“真地”回来。它在我的梦里回来过,就是我说不清楚,看不清楚的那些表情,吠声。它也在我们后来的谈话里回来过。我们说起外面捕狗的事,怎么个用圈套;怎么个剥皮;怎么个被烂木头们(指那些不良青年,有点象黑社会)下酒。说起这些,有人会怪笑,有人会沉默。本来很混乱的场景,但在我的回忆里,它们变得很有韵律感,变得“诗化”了。还有,我们学狗叫的时候,就会又想起小狗来。而我学得很象,是否是因此被认为,小狗走了,我最伤感。真的,真的有人说我对小狗感情最深的。我听了有点感动,同时有点怀疑自己:我真的最喜欢它么?
慢慢地小狗的影子从我们的中学生活里淡出了,我们忘记它了。可这几天,为何又会泛到我脑海的岸边来呢?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里面并没有因果关系,这点你该明白。
5月1日来了个中学同学,很多年没见了,与他一起聊天。
5月3 日与人通电话,从蚊子说到壁虎——大青虫——蚕宝宝——鸭子——鸡——狗——宠物狗——我的小狗。
五
我的小狗的故事要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情,确切地讲只是几个场景,自从我开始写这个故事时就出现在我脑海里了。我必须把它们写下来。先去吃晚饭。
(饭吃完了。)
时间到了高中毕业那年,天气已经很热了吧,大约比现在更迟的季节。我留着中分头,穿着白衬衣,下身一件酱色的瘦身长裤。也许是高考的压力吧,我变得更不爱说话了。我们的教室也换到了三楼,最高层,最高年级。槐树的树冠也挪到了我视线的下面。我站在走廊上,学校的围墙外面的小河一览无余。
有这样一些天,我们在上课,河对岸传过来嘹亮的歌声,女孩子的,似乎还是童声。很好听,受过训练的样子。我头就扭向窗外,很想看看那个小女孩长什么样子。
休息时间,我老一个人肚子贴着栏杆站在走廊上,常常希望这个时候,那歌声能响起来,我这样就能看到唱歌的女孩子了。后来,我真的认出了她。我每天观察着河对面的小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我真的认出了她。她好象没有在我目光下唱歌,但我确实认出她了。我就这样常常在下午,一个人在阳光的斜射下,对着对岸的小路行注目礼。她出现的时候,我就紧盯着她。一个小女孩,还没有长成熟的瘦瘦的小女孩。我希望她会察觉我的目光。真的,她真的察觉到了。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没有喊过一嗓子,我的衬衣没有折过一折,我的眼睛没眨过一眨。但她真的察觉我了。她也向我投来目光,但是距离太远了,我们几乎不可能真正地做目光交流。我们只是通过对方的姿态确信对方在注视自己。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得模模糊糊,幻想得模模糊糊。
就是这样子,我一有空就往走廊上靠着栏杆一站,一动不动,保持她熟悉的姿势。而且在那时也注意起了整洁,就两三件衬衣换来换去,但保持着整洁。我站在那儿朝对面的小路上看,我只是看而已,我并不期望她会出现。我并不期望什么,我念高三,我只是偷偷尝尝滋味。
她在那边路上出现,也会马上朝我这儿看。但她不能如我一般无所顾忌,她看我一会儿,然后转一`圈,再看。她有时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了,躲起来,她这时应该脸红扑扑的。但距离太远了,我看不清。她后来也会在我看她的时候唱歌,有时会和她的一个伙伴闹成一团。我这时是笑了还是依旧严肃,这不重要,反正她看不见。后来她唱着歌,坐上一个男孩自行车的后座,我好象有点难受。
好啦,我的故事讲完了,在这儿打住吧。前面说过要讲讲有关“医护班”的事情,还是算了吧。留作下一个故事的芽吧。
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