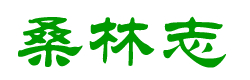在里面
by Yan
沿着墙壁我们走到尽头,果然转弯后就看到开朗的路。“你怎么记得这么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记住这些。”
我们的手没有拉在一起。
吃过晚饭,我觉得有点劲了。胃里充满着,人也容易平静。就当给你写信吧,我可以趁机想一些事情。我要说的是……说的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多日来,我没有一点说话的欲望。偶尔和某个女孩子打个电话,也是出于别种需要。我慢慢在拨开扣在自己身上的限制,爱与不爱并不重要。我希望你明白,我说这话,并不针对某个人。我想我慢慢在从这件事、所有事上脱离出来。于是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爱与不爱并不重要。这句话还是太local,我想推广到:怎么样都行。这是默而索的口头禅,就是在这种口语里,人可以发现普遍性。
而写一个故事,也需要这种脱离,这样才能使故事获得一种真实。一种围着事物的晕,它多少渗入内部,不会很多,但已足够让人兴奋。凡高在果园、咖啡馆、疯人院里作画,他在画里画下了真实。那些《吃土豆的人》,脑袋像兽类。
蚊子咬我光着的脚,我去穿上袜子。我的思路断了一下,或者之前就已经断。不管是怎么一回事,我并不怪它。像一个休止符(我其实并不知道怎么称呼它,在简谱里的记号为“0”),一个断裂给新的开始十种可能。我想到我真地不爱她了,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持续到夏天。夏天会有很多蚊子,她会穿上薄薄的裙子,我抱着她时,身体会贴得更近,她的皮肤也会更湿润。呵呵,遗憾的是我还未问清楚她用的香水的牌子。
这么多以“子”结尾的句子让上文读起来像顺口溜,不知道是我搞笑的态度造成了它,还是反过来。蚊子(文字)呵,我下午睁开眼时,见你把小肚子对着我,也不害臊。
经过那条窄路时,我一时间是明白为什么会记住它的。我没有对她说,因为我想到的是被诗人们用滥的东西,而她熟读现代诗三百首,我不想恶心她。
那是让我感觉到,经过这条窄路,就像经过通往子宫的阴道。我没说“联想”,而是“感觉”,因为我正处在窄路上,是两边墙壁和上面的一小片天空灌输给我这种印象。“联想”通常置身事外,而“感觉”是现场的。
我感到一种压迫,因而有一点快感。我想这时候应该拉着她的手,但没有。
下午本来想去买鞋的,但没有。我的鞋从买回来一直穿着,已经破得不行了。我急需一双皮鞋,最好还有一双运动鞋。运动鞋最好是蓝色的,我喜欢起了新的色调。但最后没有去。
天空的色彩非常明亮,还有那些树木,绿色也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阳光非常新鲜,女孩子们也是。她们的可爱之处也许在于,她们冬天不穿裙子。
我注意到过一个女孩子,每次见到她,总是精神抖擞的样子,兴冲冲地,像是赶什么急事。但我并不觉得她真有什么事。还有那些打扮鲜艳的女孩子,我想她们并不知道为了什么。这些事情我通常是在自行车上或者通过宿舍的窗户看、想的。我觉察到“骑自行车时”与“站在窗户后面”两者的相似性:都是一种“向外观看”。既然是“向外观看”,那么我必须处在“里面”。关于这一点,“站在窗户后面”的情况容易理解:我在屋内。而“骑自行车时”,我是通过快速运动,通过收起一部分注意力放在骑车上,来封闭自己的。这一点,你也能明白。我不大敢出去散步,因为缓步进入人群我会觉得失去保护。如果在深夜,那就不一样了。黑夜密不透风,多么惬意……
我写累了,但很快乐。
我抽了根烟,我很高兴,我想可能我终于能写下一点什么来了。我的日记本连续几次,在日期下面是这样几句话:“白天发呆,夜晚入眠/中间飘着,落不下一个字来”。我不想出门,不想撒尿。我想念我的朋友们,但不想去见他们。偶尔提起电话来拨一个号,无人应答,或者说不在,我倒是觉得轻松。今天依旧如此,但似乎能写字了。谢谢你。
今天我穿的衣服,曾穿在她的身上,上面留有一阵阵清香。昨天我把它从柜子里拿出来,有点惊诧于它保留得如此完好。我仰起头来把它蒙在脸上,我已不会像当初那样禁不住流泪,只是又一次提醒我,它还在。
这出于一种惰性。垃圾在屋内越积越多,而我从没想过把它们扫出去。我常常用手或者目光抚摸着它们,然后无奈地笑。扫出去又有何用。我不断往上面扔烟头,背对着,然后转过身来看。我常常对着它们笑,“烟头的分布/构成空间的沉默”。我也把烟盒往上面扔,好几次又把它捡起来,因为在扔出的一刹那,感觉到里面还有一根。(把那根烟从里面掏出来时,我总要暗自得意一番。)我也把漱口水往上面吐,把写废的稿纸,食品包装袋,花瓣,蘑菇,鼻涕往上面扔。有一天深夜醒来,我尿急,但不想去厕所,于是躺在床上,侧着身就尿在了上面……
今天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我们经过一棵砍倒的大树,这么大,我说可以生一年的火。她说这个林子里有板栗、苹果、草莓和山鸡。我说真是一个好地方,我喜欢,可以在这儿住下。她说她也喜欢这种地方,到处是柴火,而且很安静。
我想起那些雨后跳到路面上的小青蛙或者小蛤蟆,“尾巴都还没有掉呢”,她跟我说过的。于是我们找那条池塘边的小路。可这个城市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小池塘,但我知道和她在一起运气总会不错,所以一点也不犯愁。翻过九十九座高山,越过九十九条深河,我们来到一间木屋前。我眼睛一亮,就是这儿了!屋前立着一座门,但我们从门的左边经过。一个老奶奶在晾衣服,我想她有九九八十一岁。晾衣绳的下面有一块九寸见方的菜地,上面种着葱、蒜、土豆和西红柿……
我们没有进屋,老奶奶也没有搭理我们。我带着她从屋子的左边往里走。她说:“没路了。”我说:“有。”
今天起得很早,好久没有过了。我去打开窗户,拉开帘子,阳光洒满我的屋子。觉得不妥。于是又把帘子放下来,让它们自然下垂,中间留有一条窄缝,投在屋内垃圾上的阳光也像一条窄路。这样子,我更有“在里面”的感觉。打开的窗户让外面的声音变得响亮,也许也该关上。
从开始写这小说后,我没出过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没有一句话冒到空气里。我听到的声音是自己的,声带没有振动,信号在脑子里发出,没有出来就被脑子的另一部分接受。
这时候来了一个电话。我说话了,声带振动了,空气振动了。声音夹带着在屋内墙壁上的反射,倒还没觉陌生。我向他预告了我的小说,这就像打开了一个缺口,会影响小说的发展。怎么影响?影响的程度?还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我必须暂停,然后重起一节。
我想到那条窄路像是桃花源的入口,那个老奶奶对我们不理不睬,一定是个巫婆。天空是玫瑰色的,树木是紫色的,池塘有一点蓝。而那种压迫,那种压迫导致的晕旋是进入桃花源前必须的。进程必须有一个休止,寂静的墙让人喘不过气来,然后音乐重又响起,空间洞开。
而桃花源只能进入一次
这已是第三天,我出门了,并喝了酒。我没能保持住封闭,实在是可惜,我想我的小说写不下去了。我的脑袋里还留着酒精造成的晕。自然,我可以重新封闭自己,但不可能恢复到上文的状态。桃花源只能进入一次,第二次只能是破坏。
我认出了桃花源的入口,但正是记忆把桃花源破坏。现在才明白,那一时刻已经决定了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因为除了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我们必须选择其一。两边的墙壁干了又湿,一条裂缝张开口子又变模糊,上面的一小片天空不停地变换色彩,玫瑰红–宝石蓝–苹果绿–水泥灰……因为这,人不能永生,永生的人将目睹一切破败。自然小心地给人不多不少的寿命,并且切断一代代人之间的记忆,让他活着能觉到新鲜,然后足够快乐。
我不能继续下去了。
00/5/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