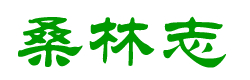龚涌
by Yan
龚涌
–读vieplivee《桃花源新记》
龚涌无意中踏在了主人公“我”的身上,不清楚“我”是不是具尸体,把“我”背到了家里。如果“我”已经死了,他会葬“我”到个该葬人的地方,桃花源里可不许人到处乱死。
“我”就这样被龚涌领入了一个新世界,过程中伴随着身体感官的接触:龚涌的脚底板,龚涌结实的背,他身上年青男子的汗味,以及发丝里薰香的气息。“我”那个时候睡着了,“死”了,恍惚之中,就是无知觉的。但感官必然是前所未有的极度敞开的。龚涌这个人物在“我”进入桃花源之初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
桃花源里没有书,不允许看书。人们说话确象是教条,除了那个被强暴的女子。这大约是由于女子的天性,以及青春期的鲜艳吧,让她无意识地有破戒的苗头。这样一个说话仅出于礼节,说话等于没说的地方,人们却是用眼神来交流的。眼神是很感性的东西,它没法控制,所以这里象是有了矛盾。但这实实在在是极有趣的事情,这样一个世界真让人好奇,我甚至觉得这个世界比我们的强。谁能保证,把人们用眼神表达的东西用文字记录下来,不会变形。意义就再不会那么单纯了,龚岛,主要是龚岛代表的那个无形的结构的权力就会更大。
这个安静的世界,说它是人类社会,不如说它是狼群。狼群的王对群体内雌性有绝对的控制。龚涌说是龚席的儿子,但极有可能是龚岛的儿子呢。这个龚涌有狼一样矫健的身材,眉目间带有英气,说他温和是不对的,他只是小心地保护内里几乎要涨满的秘密。
桃花源村民众之间,言语是不重要的,最大的用场是与从“那里”误闯进来的人交流。如果这个人在桃花源村住久了,也会慢慢省去言语。言语实在是不重要的,只需记住一些客套话就可以了。客套是言语最本质的用场吧,特别是对桃花源这样完美地运用“目光”来交流的地方。言语是他们对他们祖先所处社会的记忆。
当“我”无意中发现了“强暴”习俗之后,“我”就决定离开这儿了。与其说他是愤愤于这里的专制,不如说他是厌倦于这里的和谐。(我说上面这句话是基于我这样的认识:所谓的和谐都是单一的,可怕的。而我又这么信仰多样性。)他只是感到自己在这儿没有说话的权力,除了目瞪口呆以外,他不能用他的思想(他对他的思想极自负)去影响他人。总之一句话,他没法满足行使权力的欲望。而外面的世界,虽然他明白他摆脱不了别人以及体制的控制,但至少他能幻想他能影响别人,能多少感受一点行使权力的快感,虽然清醒一点考虑,他对外界的影响是绝不可能大于外界对他的影响的。但与在桃花源里的窒息感相比,他还是更喜欢外面世界的混乱感。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我也是。
“我”要离开,就自然而然地找龚涌帮忙。龚涌从“我”眼神中了解了这一点。从桃花源出去,这实际并不是什么偷鸡摸狗的事,但“我”却有莫名的紧张。这种紧张大约是外面的人特有的吧。
龚涌是桃花源村的异质,因他的存在而使桃花源的存在可信。龚涌是这个世界的缺口,因了他使这个世界完美。龚涌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作用,他安静地在其中生活,虽然他有不同的思想,甚至极有可能偷偷地读过不少书。(在“我”出桃花源时,身边留下的一行字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他是不可能意识到的,他只是一个漂亮的棋子,使得局面协调。
离开桃花源时,与进来时一样,“我”又“死”过去了。“我”又被龚涌,这个桃花源的沉默的异议分子和缺口,背了出来。“我”的感官又被他结实的背,青年男子的汗水,发丝里的薰香,笼罩。这一回他甚至留给了“我”一件信物:汗巾,以及手迹:那一行用桃木枝写在地上的字:“这是通往你的世界的钥匙”。
“我”是爱上龚涌了,只是作品中明确注明了“我”有妻子,那就当这是一种不限于男和女之间的爱吧。龚涌以他的身体引导“我”出入一个新世界,他身体带给“我”的刺激,就如同接吻时对方的唇一样留在了“我”身体里。再不能忘记他了,当“我”后来回忆起来,总要拿出他的汗巾看看,他的面容也会清晰地浮现出来。
类似后记:
写这个东西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有不少的惊讶。我似乎是挖掘出不少“内幕”:),包括对桃花源的评价。我一开始是认定这个桃花源是可恶的,这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不想为作品中的讽刺图像费一句话。我觉得讽刺在这个作品里的地位是不重要的,我猜,它只是作者信手拈来玩儿罢了。作者最感兴奋的,我猜,是“我”出入桃花源的过程。桃花源的喻义对中国人来说是明显的,这里除了冷酷地指明它背后的丑恶外,没有别的不同。陶渊明描述的桃花源只是他自欺欺人的幻想产物罢了。这里的桃花源也是作者满怀希望要去领略的的地方,但因作为现代人的怀疑精神,最终无可奈何地去揭露它。但整个给我的印象,桃花源与外面的世界的丑恶度是不相上下的。
另一个“大发现”是,这个作品原来也是部爱情小说:“我”与龚涌之间的爱情,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我”对龚涌的清淡的单恋。呵呵,这一点作者本人也要大吃一惊的。:)
99/5/31